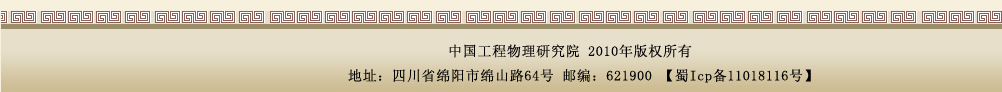朱光亚院士是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开创者,是我们尊敬的老领导,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奠基人之一。四十多年来,他主要领导我国核武器的研制和决策层面上的谋划设计,承上启下,倾心竭力。光亚同志为人真诚,学识渊博,垂范严谨,在九院前后几代人中,备受称赞。他到北京工作后,仍把九院当作自己的老家,对后来者鼓励、鞭策、情深义重。就我个人说,和光亚长期接触,当他“亦师亦友”,受益殊深。
难忘的“596”攻坚战
光亚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毕业于西南联大,1946年9月,进入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核物理,从事核物理实验研究。他发表的研究论文主要在b能谱符合测量方法和内变换等方面。1949年秋他通过博士论文答辩,1950年春就回到新中国。临行前,他满怀深情地留下了一封公开信,呼吁留美的同学们回国参加建设。

光亚1959年7月调进核武器研究所(九所,后改为九院)任副所长。1960年6月,我从中国科学院调到二机部九所二室工作后,才较好地认识了仰慕已久的朱光亚同志。此后我们就有了半个多世纪的交往。进九所后,在光亚直接领导下,我与同志们憋着一口气,为研制中国自己的“争气弹”而开始艰苦奋斗。“争气弹”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爱称,代号596。
当我知道任务和较为具体的工作内容后,既感到光荣又很感知识不足。我原是学物理冶金和金属物理的,对搞原子弹所需要的核物理知识,以及要求我转行主攻的有关炸药、爆轰方面的知识,都是外行。我向光亚同志提问求教应如何开始工作,光亚一方面传达上级精神,要自力更生、以任务为纲,摸着石头过河,边干边学,干成学会;另一方面他指出要发扬学术民主,发扬科研人员积极性,组织集体攻关,从严要求。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光亚严于以身作则,对于多学科的新知识和技术,都能学在专业人员的前面。那时,包括光亚在内的老科学家,无不谦称自己搞原子弹是外行,彼此之间切磋琢磨,学风十分可贵。
我和同志们按照领导指示,在长城脚下的17号工地白手起家,研制核装置球面同步起爆元件。两年内进行了上千次爆轰试验,初步带动了有关炸药和加工工艺以及光、电测试等的技术攻关,增强了信心。光亚同志经常冒着刺骨寒风,与老一辈科学家不时赶到实验场地,观看指导实验,给大家很大鼓舞。记得当时缺乏爆轰实验测试技术手段,光亚听说后,建议用唯象的研究方法过技术关,对我很有启发。我体会到,原子内爆是个新的科学技术领域,也是机密性很强的技艺诀窍的综合。光亚指示我们必须在研究方法和思想方法等多方面有所创新,既要注意逻辑思维分析,也要注意形象思维。当时,大家迫切希望能如期做出一个较高级的产品,所以倾心探索,奋力拼搏,不畏风险,不怕挫折,终于研制成功新的球面爆轰波聚焦元件。
我还记得许多有关炸药研究的故事。1962年和1963年7月,光亚率领钱晋教授等人到西安参加、指导与兄弟单位协同的工作。我也去了。当时我们均40岁不到,有一晚同看一台“秦腔”戏,光亚为我们讲起“狸猫换太子”的剧情,兴高采烈、历历如昨,一点不是一般人说的“寡言少语”。最近,一位老同事发现了一张当年在西安的老照片拿给我看,我很高兴。凑巧在广东珠海要召开一个“2002年火炸药技术及钝感弹药学术研讨会”,我把照片寄给了与会的战友们,他们也很激动兴奋。我感慨,时光和科技真是飞速发展啊!40年前,光亚领我们到西安开始研究炸药时的情景,形象地说,就是“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40年后的今天,我们已跻身国际研究钝感弹药的前沿了。我体会:所谓“钝感”形象地说就是研究出的炸药既“似火”又“如木”!
光亚多次到青海指导大的聚合爆轰实验。如1963年8月18日、21日、12月24日等,他与李觉、吴际霖、王淦昌、邓稼先、周光召等都去了。他们都是实实在在地进入角色,让人感到他们亲如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和指战员。有几次记得老领导刘杰去了,后来刘西尧也去过。因为光亚积累了各方面情况,所以能够写出超脱性、综合性的报告。
回忆中,我发现一件有关光亚“应时而出惊世闻”的故事。1964年6月6日,当张爱萍检查青海九院时,适值爆轰冷试验成功。爱萍同志很有感想,赋诗赠光亚同志并转九院全体同志。诗云:“祁连雪峰矗入云,草原儿女多奇能。修道炼丹沥肝胆,应时而出惊世闻。”不出所料,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应时在新疆热试验场爆响。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当夜,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和刘西尧、张蕴钰、李觉、张震寰等许多领导同志,向光亚和众多科技人员举杯。大家随杯,或干或抿,在茫茫戈壁滩上开怀畅谈,满怀豪情地欢庆中国圆了打破核讹诈的“惊世闻”之梦!
1966年以后的大动乱中,许多东西都丢了,爱萍将军遭遇浩劫,这首诗的命运,只能是依稀留在人们胸中。后来,我为了写“东方巨响的启示”一文(原载《回顾与展望》1949~1989,国防工业出版社,主编聂力、怀国模),有幸得到张爱萍来信和当面指示。经他审阅,认为上述《诗赠光亚同志并转九院全体同志》中的文字,基本上是如实的。
光亚在其他方面的技术贡献,另有同志回忆详述。我就不重复了。总的来说,难忘的“596”攻坚战是科学与政治结合的胜利。光亚善于默默无私地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包括理论、实验、工程及当时人员和物质的实际条件等,作出科学判断,承上启下,化为“集体集集体”的整体行动。光亚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完成了历史性业绩。我感到,这就是颇有我国时代特色和人格特征的历史。这里要具体举出两份光亚主持起草的文件:一是“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实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二是“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这两个纲领性文件是当时科研和试验工作的重要里程碑。也许,“现在可以说了”。如果要加以评说,我感到,在当时非常薄弱的科学和工业基础条件下,这两个文件为如期完成代号为“596”的第一个原子弹装置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国的“争气弹”不负众望争了气!
发扬学术民主 掌握氢弹原理和技术
光亚同志能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充分发挥科研人员作用。在突破氢弹原理工作方面,他在领导工作中十分重视理论,重视理论与实验的联系。他与理论部主任邓稼先多次举行技术讨论会,让理论部科研人员献计献策。他适时把北京与青海的信息沟通,让实验、设计、加工、生产各部门积极配合,及时拿出高质量产品来,为突破氢弹原理和掌握氢弹技术而努力。
1966年12月28日,我国第一次氢弹原理试验成功。我在这件事情的前后,比较多的时间只参与过青海和新疆试验的有关部分工作,但与光亚接触增多,对他的领导艺术和驾驭复杂情况的才能,进一步加深了认识。我曾听到过他向周总理汇报以及总理对他的极高评价。例如,1966年12月某日,在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听光亚汇报有关氢弹试验装置情况时,总理问(并指光亚):“报告是你起草的吧?”并指示:“多印几份送各位副主席!”
我后来才听说,还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前,在核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精心安排下,氢弹的探索就已经在原子能研究所开始。这个研究小组于1965年初调来与核武器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一起攻关。在朱光亚、彭桓武副院长指导下,由邓稼先、周光召组织理论人员和有关专家,经过认真总结分析,制定了探索氢弹的理论研究计划。经过半年多群策群力的刻苦钻研,找到了问题的关键。1965年1月,于敏调到九院任理论部副主任,9月于敏带部分同志去上海进行优化设计,得到十分满意的结果。光亚及时通知青海,九所已最终形成一套从原理、材料到构形的新氢弹理论方案,不久,即由邓稼先、周光召、于敏等先后去青海介绍讨论。在青海,则由方正知、胡仁宇、陈常宜等准备了与方案有关的实验和技术方面必须讨论的问题、计划以及工作安排。在吴际霖同志具体组织领导下,抓紧进行工作。当时,光亚发扬学术民主,考虑全面,沟通细致,在复杂的政治形势和困难的工作条件下,使得氢弹装置和试验的各项准备工作,终于在1966年12月28日以前完成,保证了氢弹原理试验胜利完成。
试验完成后,聂荣臻元帅即在基地召
开座谈会,部署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任务。有钱学森、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等科学家及张震寰、李觉、张蕴钰等领导参加。与会同志都建议为加快氢弹试验速度,采取与这次试验相同的结构,设计全当量装置,尽快进行全威力的氢弹航弹核试验。此时,全国已处在文化大革命的态势下。作为技术干部,虽然得到周总理和聂帅的保护关怀,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我们唯有凭着赤忱的爱国思想,无私地努力工作。光亚担子最重,北京青海两头跑,有时忙过头了,不想吃东西。如果我在旁边,总要提醒他,“吃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这话自然也是嘲讽我们自己的。由于我们始终保持积极、乐观和信心,终于成功地于1967年6月17日在世界上先于法国1年时间,成为拥有氢弹的第4个国家。
在任何时候 不改学者本色
1970年,光亚调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以后,仍然对九院的核武器研制给予亲切关注。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在世界上5个核国家中,中国是进行核试验最少的。为了仅进行少量核试验就设计出先进的核武器,他要求我们加强创新意识、不断提高科技、学术水平;要善于掌握和运用辩证分析的方法,抓住主要矛盾。在制定核试验规划时,要抓住主要矛盾,有所为有所不为。
光亚特别重视搞好战略研究,他要求一次一次深入开展有关战略和技术能力的研究。例如,如何“一次试验,多方收效”的问题,就是一个程度不同而“可贵难能”的问题,核试验的热测试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可贵难能”。
我深感经过核试验在思想上比技术上有更多的收获。试验前,九院、核试验基地等很多单位的科技人员,在新疆一个封闭的地下平洞内,为了新的理论探索,设计安放了多种创新的测试记录探头,希望在核爆炸的瞬间,用这些探头“抓住”中子、光子、电子等诸多物理参量,难乎哉!试验后,他们好不容易“抓住”了这些东西,但这些东西的凭证,只是千奇百怪的、记在照片上的“曲线”,有时还要排除干扰,才能判别分明,这又是一个难题。至于判明正确与否,最后要能与理论预估和实验的修正比较,才能作结论。这是最难的了。难,难,难!对于那样难以取得的成功和胜利,我从内心想欢呼歌颂我们的“神工”们!在这次试验后,我有感而发,写了一首打油诗:风雷难测神工测,诸子百家瓮中鳖。甲骨文字判明时,锦囊妙算昭日月。
我想指出,在核试验前后,光亚都是以一个普通科学工作者的身份出现。试验后的长时间里,光亚也总是多次和大家一起总结。1994年3月,光亚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我听过他在人民大会堂所作的呼唤尊重科学的大会发言。后来也在不同场合听过他多次讲话和发言。总的来说,我感到他实事求是,不说大话,不说假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总是以一个普通科学工作者自居,与当官前基本一样。
周恩来和不少领导同志们,都曾称誉光亚同志有“立德立功”之优良品格。但光亚自己,他还是他,默默无语地保持着本色,坚持不懈地为祖国强盛、为核盾向着有利于世界和平的方向奉献自己的心力。一次,光亚全神贯注地听着一位美国教授作有关裁军的讨论发言。一贯认真只听而不多说的光亚同志,竟有兴趣发言问这位教授:“美国有多少科学家主张彻底销毁核武器啊?”当时我联想,光亚是在“踏雪寻梅”啊。
过去国弱挨打,现在国强人荣。九院人特别是老同志对此深有共感共识。所以在1992年的一次年会上,光亚提出一个集体赋诗的创意,要大家互勉再做奉献。光亚命题后让我打个草稿,写写大家想的。那一天,人气很旺。我也就遵命,打油献丑,不计工拙了。写成,光亚作了仔细推敲,然后,由与会代表约30人审阅赞同签名,词曰:“五世聚新堂,喜气洋洋。绵山蜀水迎秋光。科技不畏崎岖路,前景辉煌。人事有沧桑,激荡昂扬。许身为国最难忘。神剑化作玉帛酒,共创富强”。此词调寄浪淘沙,后在院里传开后,首句“五世聚新堂”成了题名。
从这件事,我发现光亚是颇有文采而不轻易外露的一位长者。当然,我感受最本质的一点还是,他在任何时候,不改学者本色。
我曾担任863激光技术主题第一任首席科学家。光亚只要有时间,总是尽可能下来参加我们的讨论。我曾同时兼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因而有幸有更多的时间听光亚的指导和教诲。我不能不在这里提到最受人尊敬的钱学森先生,钱老的学者本色和高风亮节,光亚经常提到,并诚恳指出,钱老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也曾有机会参加光亚和他的好友李政道的几次聚会。印象最深的是1995年6月的端午节,李先生宴请国际会议的朋友,在“来今雨轩”的雅间,我聆听着政道和光亚闲谈《楚辞》里“天问”中“九天之际,安放安属?”原屈原词中的一问一答,化为今晚科学家之间的求索了,真令人感到趣味盎然。
回顾半个多世纪,弹指一挥间。每次重温光亚优秀品德,平易近人,我就想到用“温、良、恭、俭、让”五个字来总结。他领导我们搞了“一点”两弹,现仍在这个领域,为了国家安全,迎接挑战。光亚已届耄耋之年,身体健康,精神饱满,情态潇洒,戏称自己的健身法宝是“喝酒、吸烟、不锻炼”。当然,人们会了解光亚的真实意思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反之亦然”。
(文/ 陈能宽 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