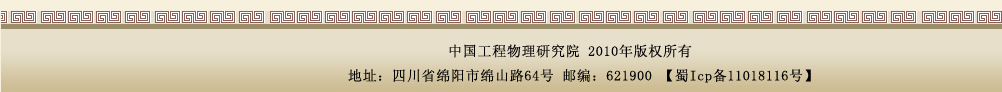朱光亚院士是我们的老领导,是九院的奠基人之一,是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开创者之一。我国两弹的研制成功和发展凝结了他的全部心血:以中国式最快速度、群策群力突破两弹;高瞻远瞩,掌握主动,瞻前决策,突破地下核试验技术;狠抓两弹结合武器化,形成战斗力;亲自组建专家组,重视近区物理测试和放化分析;重视核试验总结和再分析;深谋远虑、运筹帷幄,走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
朱光亚早在青年时期,就与核事业结下不解之缘。抗战胜利后,刚离开西南联大校门的朱光亚在吴大猷先生竭力推荐下,与吴大猷及李政道等几位同学赴美学习原子能科技。此学习计划后被证明仅是中方的一厢情愿,朱光亚便转到在密执安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学成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大学、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任教,培养共和国首批原子能技术人才。当国内筹建原子能事业时,被选去开展反应堆物理研究,他是我国点燃启动第一座反应堆的现场负责人,1956年担任原子能所初建时期的中子物理研究室副主任。
20世纪50年代正当我国决策自力更生研制“两弹”时,在原子能所钱三强所长组织指导下,朱光亚早已介入原子弹理论研究,经常参与研讨,进行原子堆及原子爆炸临界质量计算等研究。1959年7月,周恩来总理向二机部部长宋任穷传达了中央关于“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的决策。钱三强受宋任穷委托,协助物色核武器研究所技术领导人选,钱就推荐了当时在科技界富有才华约34岁左右的朱光亚,担当核武器研究所技术副所长。认为他年富力强,精力旺盛,有较高的业务水平和判断事物能力;有较强的组织观念和科学组织能力;能团结人,深受老中青科技人员的拥护和尊重。
根据当时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苏方于1958年4月和7月曾派出过两个专家组来二机部九局工作,第一组7人于4月来自列宁格勒设计院,协助选场及基建设计;7月第二组3人来自阿尔扎马斯核研究中心(专家组组长E.A.聂金;以及理论家B.E.加费利洛夫和马斯洛夫)。加弗利洛夫在访问原子能所时,向当时九局领导吴际霖竭力推崇朱光亚是一位十分有头脑、能力很强的青年科学家,他说他本人不认识朱光亚,而是来华前塔姆院士(1958年度诺贝尔奖获得者,苏联核武器研制参加者)向他推荐的。可见当时正年富力强的朱光亚在国内外学术界己有相当的知名度。
1959年6月20日,苏联毁约停援。我国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力以赴调集科研骨干力量,相信和依靠自己的科技力量,一定能打破美苏核垄断,自力更生搞出“争气弹”。就这样,朱光亚于1959年7月调到九局,任技术副所长。实践证明,朱光亚院士在我国核事业发展中起了主心骨的作用,很好地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做出了卓越贡献,成为我国国防科技战线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
当历史进入20世纪50年代时,美苏核军备竞赛方兴未艾,核武器研制成为大国发展的战略重点,成为世界力量平衡的砝码,成为国际政治、外交、军事斗争的工具,成为决定世界战争与和平的重大因素。中国有了核武器,势必动摇当时两个超级大国核垄断地位,打破世界格局的力量平衡。两个核大国相互勾结,对我国进行核威胁,妄图对我进行“外科手术”。1963年还搞了三国部分禁试条约,企图保持其核优势,遏制我国核武器发展进程。
朱光亚到九所后,我国核武器研制技术层面的组织和决策就落到他的肩上,这副担子从来没有轻松过。根据当时我国国情、国力、经济和科技现状,要想在短期内搞出原子弹、氢弹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但当时面临的国际形势却是美苏进行核讹诈、核威胁。
早在建国初期抗美援朝期间,美国就试图对我进行核打击,美国第七舰队占领台湾海峡。国际间核武器竞争激烈,英国也有了原子弹,法国正在研制。毛主席和党中央审时度势、果断决策,中国为了寻求战略安全,别无选择。毛主席1956年4月4日“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在1958年6月军委扩大会上又说:“原子弹就是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我们只要有了人、有资源,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从全国各条战线调集迫切需要的科研骨干力量是首要任务,1960年开始经中组部从中科院、高校等单位和部门点名选调几批高中级科技人员,后又将原子能所王淦昌、彭恒武等科学家调北京九所,基本形成了科技领导和骨干力量。
1960年组建了8个研究室,一个加工车间。同年5月份扩展为理论部、实验部;设计部、生产部、下设13个研究室。朱光亚重任在肩,全面负责科研管理和组织协调。当年9月朱光亚主持执笔编制两年规划和上报的两信件“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初步建议及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明确提出试验分两步走。
1960年10月10日,刘杰、朱光亚向聂荣臻副总理等汇报九局原子弹规划设想时,明确提出:1963年完成缩比尺寸模拟实验;1964年二季度进行综合演练,紧接着完成首次试验任务的准备。
1960年4月28日,在北京长城脚下工程兵试验场17号工地,建立爆轰试验场,打响了第一炮,揭开了核武器爆轰实验研究的序幕。1960年10~11月九局成立4个专家委员会。彭桓武与朱光亚担任中子点火委员会正副主任。朱光亚兼管三室工作,当时三室担当了3大关键任务:研究点火中子源;核武器装备的临界、次临界、核安全问题研究,以及核试验物理、放化测试任务。
在进行零功率实验和次临界装置研究时,经历了1年零3个月的上千次实验,取得了第一手数据和初步经验。朱光亚同志经常在现场与一线科技人员切磋和决策物理实验内容。这期间,17号工地上以王淦昌、陈能宽为首的科研人员通过上千次爆轰冷试验,成功地完成爆轰球面波聚焦元件设计和试验研究,朱光亚有时也亲临指导,建议用唯象研究方法过好测试关。
九院建院初期,经过千百次实验之后积累了大量数据和经验,并在科研实践中充分体现出了理论和实验密切配合的动人场景,上下齐心、团结拼搏、群策群力的精神面貌。朱光亚虚心听取不同方案和意见,经理论与实验多次反复研究论证,形成决策意见和实施方案。朱光亚在“两弹”突破期间,坚持科技民主,坚持理论与实验相结合,集思广益,使我国核武器研制在效费比、安全性和发展速度等方面远远超过了先进的核大国。这是与他的卓越领导才华和精心策划分不开的。
核试验是检验核武器理论设计的主要方式,核试验实验诊断是获取试验结果的唯一途径。1957年9月19日美国在内华达进行了首次封闭式地下核试验,随后,苏、英、法也分别在1961和1962年开始进行地下核试验。1963年7月美、英、苏联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妄图通过禁止大气层试验来阻止中国核发展。这是我国两弹突破早期,国际外交斗争面临的新形势。
为了粉碎核大国的阴谋,我国要尽快发展核武器和核试验技术。朱光亚同志深谋远虑,在1963年7月发表的文章《停止核试验是一个大骗局》中,在分析美英苏三国核武器发展情况后,朱光亚指出:他们宣传部分禁试条约,大力发展地下核试验的做法,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发展核武器,并遏制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
1963年9月,当时我国首次核试验尚未进行,根据朱光亚建议,二机部与国防科委就我国进行地下核试验问题作了初步商讨,接着中央专委12月做出了决定。1964年2月28日,基地就打报告开始地下试验的勘察和准备工作,经过不到五年的场地试验工程和测试技术准备,1969年9月23日我国进行了首次地下平洞试验,为我们及早掌握地下核试验技术及发展核武器研制争取了主动。
在王淦昌、程开甲、朱光亚的领导下,我们亲身经历了试验准备的全过程。朱光亚是首次地下试验现场七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当时我国己有能力,同时开展两场核试验的现场技术准备。首次地下试验后时隔6天(即1969年9月29日)下午16:40,在戈壁滩又进行了空爆氢弹国家试验,核试验组织工作是在当时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进行的,克服了重重困难,全面完成了任务。
凡遇现场试验朱光亚同志总在现场,不论酷暑严寒和我们一起,同吃、同住、同钻军用帐篷。新疆戈壁沙漠的试验场生活十分艰苦,张爱萍同志曾形象地描述现场条件是“饥餐砂粒饭、渴饮苦水浆”。
1969年9月,朱光亚在戈壁滩与我们一起准备两场国家核试验。一天下午狂风大作,天昏地暗,飞沙走石,无法辨认东西南北。我们在空爆现场只得临时停工,紧急返回驻地。但风沙模糊了方向道路,汽车窗玻璃被完全打毛。队伍中3至5人手挽手组成人墙,引领汽车向前开路。
回宿营地仅8公里的路途,我们的汽车却足足开了4个多小时。回到宿营地看到有的帐篷被掀了顶,我们折腾至午夜二时,在被掀了顶的帐篷里,缩成一团过了夜。当时我们的院领导毫无例外和大家一起同甘苦,唯一优待他们的是帐篷内多了一只尿壶,算是照顾他们晚上不至于为了方便而走出帐篷。
竖井试验是地下核试验的另一种方式,地下井地质条件复杂,有干井、有湿井、深水井等不同状态。在一个场区可打很多个井,场区可充分利用,根据不同井深试验不同大小当量。但钻井建井周期长、技术难度高。不同于空爆和平洞试验。由于建井尺寸限制,核爆测试空间比平洞要小很多。
在竖井狭小的空间内,要做到一次试验同时针对多个辐射体物理过程的测试,达到一次试验多方收效,实非容易。但是,在朱光亚的精心思考、果断指挥和谨慎决策下,确保了每次试验的万无一失。
早在首次核试验前夕,1963年12月5日,中央专委在广泛听取意见基础上,决策“核武器研究方向,应以导弹为主,空投为辅”。从1964年开始,在朱光亚同志带领下,于3月下旬九院就派出协调组,全面了解导弹性能,开展制定产品工作,拉开了第一代导弹核武器研制的序幕。
1964年11月,朱光亚又带领九院的协调组到五院协调计划进度。1966年2月,经有关部门会商决定,在中央专委决策下,于1966年9月在我国本土上进行飞行状态下的两弹结合核弹头冷试验,随后于同年10月27日进行史无前例的、历史上美苏等核大国在本土上从未进行过的导弹飞行原子弹核爆全当量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体现了我国高层决策者的战略意图和超人胆略。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国核武器研制面临新的挑战。要进一步小型化,加快研制新型核武器和中子弹探索,客观上迫切需要提高核爆炸近区物理诊断和放化测试水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朱主任高瞻远瞩,提出并亲自筹划组建核试验专家组(近区测试和防化测试专家组),随后建立了工程专家组。
朱主任通过专家组协助制定核试验具体实施计划和规划;分工和研讨技术关键;进行核试验的数据分析总结和学术交流;及时调整决策措施。这种机制是一种创新机制,通过这种组织形式听取专家群体多方面意见建议,群策群力,发扬学术民主,对确保历次核试验高效、高成功率和提高测试技术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六五”期间,我国核武器研制取得两项重大突破,即新型核武器及中子弹原理试验成功。在理论与实践密切配合下,核试验实验测试技术也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进步。
朱光亚同志不仅是专家组倡导组织者、指导者也是参加者,在召开专家组会时,他每次都力争亲自参加和指导。在他建议下,1982年4月,在上海举行了首次核试验物理测试技术研讨会。他到会讲话,强调要科学院、高校和工业部门,大力协助解决武器研制和核试验测试面临的新难点,如探测器件、电子设备、传输电缆、标定源建设的研制和定点合作等。
九院同志在现场亲自感受到他作风踏实、深入细致、果断决策,在试验现场多次化险为夷。如1971年12月30日进行空爆试验,飞机在飞行中弹投不出去,朱主任当即与在现场的兰空副司令员杨焕民磋商后,镇定自若,亲自指挥飞机带弹着陆,成功地排除意外故障。表现了科学家和领导人坚定负责、无所畏惧的精神。
1975年10月,第二次平洞地下试验时,九院首次上气体取样放化测试项目时遇到多种困难和阻力。朱主任关注着取样成败,在听取了汇报后,指定由傅依备带队派第二批人员再试。因抽气泵电源已断,他要求带小型发电机。第二次进洞仍未取到样品,但确认埋入的取样管被压实,无法取到内部气体产物。此刻,朱主任仍关注此事,他走出工棚站在高处了望,突然发现洞口旁的支洞口有一股浓烟,他认定这里可取到有价值气体样品。在他的鼓舞下,取样人员先后两次进去取样,最终取到两瓶极有价值的气体样品,得到这次试验的放化测试等数据。从此气体放化分析测威力的方法得到现场确认。该方法也成了放化速报威力的常规例行法,在日后核试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做地下试验时,有时工程上遇到用作电磁屏蔽的钢球不慎落到产品罐里去了;另有一次现场竖井试验万事俱备,已可将试验产品吊装下井了,突然发现断了几根测试电缆;又有一次竖井试验,产品已开始吊装下井,却遇到需重新评估计算产品当量的安全上限等问题。
有人说几乎每次热试验在现场总要遇到工程技术上意外的“卡壳”,但朱主任总能引导大家群策群力、排难解危!我院在核武器研制方面多次取得了里程碑式的重大突破,每项成功都渗透着朱主任的心血、汗水。他几乎每次必去核试验现场指挥,他是我国核试验技术领导去现场次数最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朱主任极为重视历次核试验的总结和数据分析工作。在每次国家试验后,总是及时召开数据分析专家组会,通过数据分析对比得出对试验的正确评估,找出差距和问题,以利承前启后,及时提出下次核试验任务的技术要求,进一步调整和明确核武器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在数据总结分析基础上,制定新的核试验规划,即使在文革期间,朱主任也排除干扰,组织了多次核试验数据分析会。如1972年8月在北京开的三次核试验核数据分析会,1976年底在宝鸡举行的地下核试验分析会。朱主任多次讲话,要大家力戒骄傲,“要认真总结经验,有实践就要有总结。我们科研工作最大毛病就是总结不够。要通过实践总结提高上升到理论,再去指导实践。从1964年以来,已响了14次,我说过多次,要总结经验。大家忙忙碌碌,但是像样的经验总结很少”。他还说:“你们正处于30多岁年纪,正是好时光。每次试验花的代价很大,要认真总结经验,避免失误才对呀!”。他身体力行,1996年全面禁核试后,更加重视和加强当前进行的核试验数据再总结、再研究和分析工作。
20世纪80年代,朱光亚敏锐地预感到高科技竞争,面临国际全面禁核试的影响,他反复强调和要求九院同志必须跟踪当前国际高科技发展前沿,精心思考为国家863高技术计划的先期论证作大量充分准备。这些工作为中央起草和决策“863”计划纲要和实施纲要,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后,迅速组建了以创新为宗旨的跨学科、跨地区、跨行政的吸引优秀人才的精干攻关队伍。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及1992年朱光亚主任组织我院领导向中央汇报,审时度势、及时决策加快核试验步伐,以迎接CTBT全面禁核试的挑战。鼓励我院充分利用和发挥已有的技术基础和能力,投入高技术前沿攻关。
朱光亚院士以其远见卓识和中国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呕心沥血,时而幕后策划,时而台前指挥,走出了一条效费比极高的、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核武器之路。
面向21世纪,中央领导提出:“在发展精干有效的核武器基础上,建立可信的核战略威慑。”反思今日国情与20世纪50年代的国际环境,确实面临新的挑战,“我们发展战略核武器,不是为了进攻,而是为了防御,是积极防御”。中国需要和平的环境,但和平的环境需要自身的综合国力和国防实力。
最近几年朱光亚主任虽然日理万机,仍在百忙中几乎每年都来九院,亲临第一线指导工作。2003年2月,参加我院发展战略研讨会,他深刻分析当前形势,明确指出我院今后的方向和任务,要求我院力争在短时期内基本或初步掌握不依赖核试验的研制和发展核武器的能力,拓宽领域,开拓创新研究,应对国际上各种挑战;培养新一代人才队伍,保证后继有人;面向21世纪头20年,要抓住大有作为的战略发展机遇期,告诫我们要立足长远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
以朱光亚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为后人做出了榜样,他们以强烈的爱国之心为动力,在两弹事业中创造了人间奇迹。朱光亚坚持学术民主,求精、勤奋、奉献的精神,导演了一幕幕核试验高成功率的奇迹。他一再提醒我们:九院是在全国大力协同下完成这些任务的。总结工作要科学、要实事求是。核试验不能说我们是一次成功,或者说次次成功,这样说法不科学。我们也有过失败,也有过不太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但我们的成功率较高,我们有能力把核试验的不成功率降到最低。
回顾我国核试验所走过的历程,我们永远珍惜老一辈革命家和科学家留给我们的无价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将其继承发扬、继往开来、永不懈怠、奋斗不息。
(文/华欣生 傅依备 徐志磊)
华欣生 研究员,曾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科技委秘书长;
傅依备 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科技委副主任;
徐志磊 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总工程师。